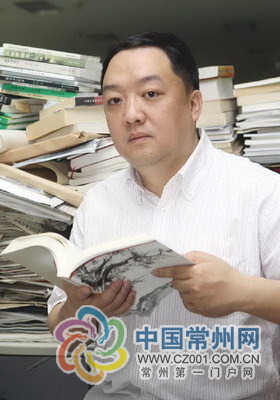
圆圆的身材,圆圆的脑袋,一身正装,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正襟危坐的男子曾是拼命攒钱购买原版卡带,辗转上海、常州搜罗打口碟,飞驰在常州第一座同济立交桥上,哼着《马路天使》的追风少年?
他是叶舟,土生土长于常州,求学于复旦,现任职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兼任上海社科院图书馆文献部主任。叶舟的研究以明清时代江南地带的社会文化史、城市史、历史文献学为主,曾在《中国地方志》、《史林》、《社会科学》、《明清小说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多家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常州是他研究的重中之重。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便是——《清代常州的城市社会》;他参与写作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常州卷,2011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不久,叶舟有三部重头戏即将面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5万字的《繁华与喧嚣:清代常州城市社会》、35万字的《常州民俗文献汇编》第一卷第二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00万字的《清代常州文人年表》……
两弃金饭碗 不走寻常路
叶舟的求学之路并非坦途。
他曾是叛逆少年,和很多文青一样,中学时期严重偏科,数学经常不及格。回忆往事,叶舟笑道:“后来我发现我不是学不好数学,而是不喜欢当年的数学老师,以至丧失了学习兴趣。”1989年,叶舟高考分数超过大专线,至今看来颇为吃香的财会、金融、计算机等专业,却都不入叶舟的“法眼”,他选择了复读,复读一个多月后,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开始职场生涯。
叶舟并未就此放弃他的求学梦,他一边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一边坚持自学考到了中文系本科文凭。1997年,公务员面向社会招考,叶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却意外地考入了常州市贸易委。2002年,贸易委面临机构调整,有政策鼓励大家分流深造,叶舟毫不犹豫报名考研,事后他得知,全市只有他一个人申请脱产读研。叶舟并非一时冲动,也非书生意气。他说:“自1989年高考之后我就给自己订了一个计划,什么时候念完本科,什么时候考研,什么时候读完博士。我曾经的理想是当个作家,但又感觉小说无法改变世界;从高中起我渐渐萌发当历史学家的想法,做思想史这块。贸易委的机构调整只是给了我一个契机而已。”2002年,已过而立的叶舟如愿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巴兆祥和王振忠,硕博连读。
2008年,叶舟博士毕业,面临金融风暴中就业艰难的局面,他也曾徘徊,“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的,如果不能进入上海最好的研究机构(复旦或者社科院),我只能放弃做学术。”叶舟参加了公考末班车,并成功进入面试。这时,峰回路转,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叶舟再次选择了学术。
在故纸堆中发掘常州的多重名片
叶舟的父母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医学院),母亲是上海人,他却土生土长在常州近30年。所以他特别强调“我不是为了来上海而做学术,而是为了做学术而来上海,上海始终不是我的家。”叶舟的学术研究和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常州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积淀也给叶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养分。
常州致力于打造“爱心之都,慈善之城”,首创“慈善常州模式”,在叶舟看来早就有迹可寻。据叶舟介绍,常州最早的慈善机构可以追溯到明代东林党发起的“同善会”,这也是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这是一个由乡绅、文人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有着浓厚的理学与道教色彩,每年用征信录公布所有的账务明细,每天用功德格记录一天得失。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逢年过节施粥、灾荒年赈灾等,同善会还有个特殊的慈善功能——惜字——“把地上有文字的纸头捡起来,好好珍惜”,不知是否与常州盛产文人有关。清代之后,官办慈善机构与民间慈善机构合流,常州形成了以育婴堂为首,东西同仁堂、南边怀仁堂、北边存仁堂四大机构分区管理的一整套慈善体系,100余个分支机构遍布城乡各个社区,并在全国首次针对“推浮尸过界”这一陋习,提出了处理路毙浮尸的办法,填补了当时的管理空白,有效地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
叶舟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与常州有关的知识分子的境遇尤为关注,“抛开那些学术成果、诗词歌赋,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只是更聪明一点,文笔更好一点,我关心他们怎样聚在一块,怎样赚钱,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提到常州的知识分子,必然绕不开苏东坡。苏轼虽不是常州人,却给常州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乾隆下江南时,常州文人智囊团以赵翼为首商量要建造一座别出心裁的标志性建筑,便有了舣舟亭。乾隆游完舣舟亭后大笔题诗,太平天国后,御碑倒塌,当年的行宫也不复存在。现在,大多数常州人都知道舣舟亭与苏东坡,但又有多少人记得乾隆的题诗呢?”皇权与文化的较量,孰胜孰负,由此可见一斑。
“与同属江南的无锡苏州相比,明清时期的常州经济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近代,以漕运为中心的奔牛逐渐落后于以手工业为主的湖塘桥,常州经济落后于无锡苏州都与行政化过强有关。常州人南人北相,宋末被屠城只余18家,太平天国,常州有5-6万人战死或者跳楼、跳井、跳河自杀,按照当时的总人口,约等于50%的常州人死于战争……”谈起常州的历史,常州人的性格特点,叶舟滔滔不绝。在故纸堆中不断发掘历史的真相是他做研究的原动力,“我不能说我说的就是真相,只能说是无限接近真相。”叶舟正色道:“这几年我一直在大量收集地方文献资料,比如清人日记五种,即丁嘉葆日记、张曜孙日记、庄鼎臣日记、庄宝澍日记、恽毓德《壬辰春试记》等,下一步我希望从文化、教育和家族社会等方面讨论常州城市社会的近现代化转型以及江南城市和上海的互动关系,如常州人在上海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活动对家乡产生的影响等等。”
请不要叫我学者
虽然顶着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的高学历,不断着书立说,但叶舟并不太认同自己的学者身份。他不断地说“请不要叫我学者”。在他看来,学者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责任,而他,更愿意躲在史料背后,关心一下自己有兴趣的“历史八卦”。他做研究,更像是在玩,就像他从小喜欢躺着看书却也看不坏的眼睛是天生的,报出一连串地名人名的惊人记忆力是天生的,沉湎于史海钩沉还是天生的。
叶舟毫不讳言自己推崇的当代历史学家极少,“很多大众眼中的名人在圈内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学术价值”。叶舟非常羡慕陈寅恪、姚大力类型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一脉相承,在研究中既能运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又能运用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方法,用死去的语言重新研究史料。“复旦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便是可以和很多大家学语言。”常州先贤吕思勉是叶舟心目中的“标杆”,“吕思勉体现了常州文化学术的精华,他对整个中国思想史有贯通的了解,又能结合西方现代的学术观点”,叶舟解释说,“做历史研究最难的是从众所周知的史料中提炼出新的结论,这必须对所有史实有纵深的了解和独到的思考。”
叶舟的业余生活简单而丰富,读小说听音乐看美剧,整一个“宅男”。为什么语文功底这么好?“几乎都是课外书读出来的,读过无数本苏联名着,最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是我第一次通宵看书。”
“喜欢一些老的歌手,比如达明一派。我到复旦读书后发现很多小男生小女生也追黄耀明,有些人是为了显示自己小资而不得不去听达明。我对他们则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因为他们完全是我同时代的歌手,十六七岁听《马路天使》,感觉歌词唱的就是自己……”现在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我已经老到没有力气再去喜欢一个新的歌手了。”虽然,男人四十是最好的年华。
“偏爱科幻、侦探推理类的片子,比如《X档案》、《犯罪心理》啊,《名侦探柯南》当然也看,还有东野圭吾、松本清张的……”叶舟大笑,现学现卖了一个伍迪·艾伦编的吸血鬼冷笑话:“德古拉伯爵(吸血鬼祖先)敲邻居家的门,邻居很惊讶地说你从来没白天出现过,德古拉说现在明明是晚上我很饿我要吸血,突然太阳出来了,德古拉被烧成一堆灰烬,留下目瞪口呆的邻居,原来刚刚是日全食。”
叶舟,从一个追风少年到学术宅男,“翻阅的史料可以堆积成一人多高”,多少艰辛消饵在轻描淡写间。
叶舟,一叶扁舟驶向浩渺的史海,现在,仅是刚刚起航。 |



